2017-11-14
当画家阿努尔夫·莱纳(Arnulf Rainer)用激烈粗暴的笔触在画面上涂抹时,他充当了这个领域的先锋角色。换句话说,他不是在描绘脸,而是在对图像发起攻击,他企图将脸从图像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一种自我表达。在通往脸的道路上,图像被破坏或者说被加以转化。这些干预表明,莱纳对脸的处理手法构成了一种图像批判。早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就尝试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复绘,这些面目全非的作品通过某种“不在场”对我们施加影响。“涂抹”与“复绘”使图像封闭起来,犹如一张缄默不语的脸,其中隐含了对作为传播对象的脸部图像(而非对脸本身)的批判。在莱纳的初期作品中,观者只有通过标题才能了解藏在黑色颜料层下的乃是一颗“人头”。这一点随着莱纳的“头部复绘”系列而发生改变,后者揭示出作品中的一种双重在场:照片与绘画,原有图像和新生图像。面对“头部复绘”系列,观者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只有当我们在画家恣意泼洒的笔触中捕捉到某种情感甚至是愤怒的痕迹时,才产生了画面中的脸。
荒谬的是,经由脸的遮蔽恰恰形成了一种新的在场,它是莱纳从大众媒体泛滥成灾的脸那里重新召回的一种在场。画家与脸展开了一场暴怒的对话,他对现成的廉价照片做了大胆破坏,以此来标举脸的价值,对如同廉价货币一般俯拾皆是的摹写发起反抗,并借助新的媒介,让脸和图像的古老戏剧重新上演。莱纳“背离”绘画、投身“后绘画之绘画”的意图,创造出了肖像的反例,而作为一种绘画体裁,肖像本身的市场价值早已一落千丈。在莱纳的作品中,自发的绘画行为战胜了图像,粗暴激烈的动态战胜了仅仅作为摹写而发展至今的再现。
莱纳曾在60年代创作过一个脸部系列,他在其中以暴躁或反讽的方式对自己的照片进行复绘,而与此同时,他对脸的迷恋也愈加深入。在《脸的滑稽剧》(Face Farces)中,为了对抗相片中表情的僵化,艺术家在拍照时扮出各种鬼脸。绘画行为最终战胜了影像。1977年到1979年期间,莱纳出人意料地将死亡面具作为唯一题材(图1)。但在这组作品中,他同样是在一步步地向脸逼近,力图揭示出脸的僵化与脸部再现方面的传统惯例。在脸自我闭锁、化作一种绝对的表情,进而完全消融的一刻,死亡与生命构成了一条敞开的界限。正是在此意义上,班卡尔才将死亡面具称作“人的终极图像”。

当莱纳对死亡面具的照片进行复绘时,他提出了脸的图像特征这一核心问题:只有当一张脸变为面具的时候,它的图像特征才得以显现。脸部一旦摆脱了所有转瞬即逝的表情,其图像特征便会前所未有地呈现出来。莫里斯·布朗肖切中肯綮地将裹尸布称为“它的专属图像”。莱纳取消了我们观看面具时的距离,并通过粗暴的干预迫使面具重获生机。他的双重策略在于,剥夺死者的摹像与任何一种再现的价值,并以粗犷暴烈的笔触重新捕获仍旧从那张脸上散发出来的生命气息,而这一切都是在对死者的脸施加暴力的这样一种“破坏圣像式的”行为中完成的。

我们或许有理由猜测,莱纳感兴趣的并不是面具本身,他只是在寻找各种机会来观察垂死中的人脸,以便通过一种触犯现有社会禁忌的方式来接近脸的真相。事实上,每当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死者时,他都会用相机直接对死者的面部进行拍摄,将这些照片形成系列并与死亡面具置于一处,仿佛试图借以展现同一种东西。1978年他曾为维也纳举办的一个死亡面具展撰写过一篇评论,这篇内容详尽的文章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经过十年艰难的自我描绘后,死者的脸部语言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能打动我。”用他的话来说,此时的自我描绘进入一种“直接的、无脸的”境界,呈现出一种“无动于衷”,“仿佛这就是最终的形式和结局”;这是“缺席者的面容”,它“使人们几乎难以接近死亡的真实面貌”,对于这样一张脸,面相学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其原因在于,有这样一种图像,它虽未揭示出死亡的真实面貌,却通过对象的缺席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和脸之间(或表现在脸上)的那层隔膜。在莱纳那里,图像概念和脸密不可分,譬如它意味着我们所拥有的只能是脸的图像,且我们清楚它始终是图像,永远不会变成脸。也就是说,在图像可展示的范围之外,我们还想看到更多的东西。图像概念蕴含了再现和不可再现性的分裂,同样的分裂还体现在可见性和在场之间。在图像中显现并不等于在场。图像再现的是一张不可再现的脸,每当人们想要记录这张脸时,它总是即刻变为面具。在任何图像里都会不期而遇的那种界限,让莱纳深感失望,他正是带着这种失望来对死亡面具的照片——它们仿佛是面具的面具——进行加工的。他的笔触即是他的姿态,其中注入了比照片所能捕获的更多的生命力,同时它们又是针对照片上的人脸——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平滑表面——而发起的一场暴力行动。
生于1940年的美国艺术家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将脸作为毕生的创作题材。在这一点上,他与莱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同时又与后者形成了可以想见的最大反差。这种反差始于他们二人对照片的处理方式:莱纳通过一种类似于破坏圣像的行为,对照片进行干预,将其涂抹至面目全非;克洛斯则每每像是在举行一场细致入微的仪式一般,为他的模特拍摄一系列快照,再从中遴选合适的绘画素材。有一幅照片记录了1970年他为友人凯斯·霍林沃思(Keith Hollingworth)绘制肖像的场景(图3),从画面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将照片一点一点地转为大尺幅,仿佛是在将一张照片转化为绘画,或是对一张照片进行描摹。他的画甚至保留了照片的黑白色调,由此形成了一个不是照片却仿似照片的混杂作品。此外,它还是一件巨幅作品(273.1cm×212.1cm),类似尺寸直到70年代才通过摄影技术得以实现。但克洛斯否认自己只是在复制照片,他表示,照片仅仅是为创作提供了一个方向,他不想让有生命的脸萦绕在自己周围。照片在此只是充当了一种模特的角色,图像是通过画家对人物的独特观察而逐渐充实起来的。

克洛斯并没有像莱纳那样去揭示隐藏在绘画面具背后的脸,而是揭开了描摹的面具。他的巨幅画像摒弃了历史上肖像画的标准比例,画面中的人脸超出了任何一种适于画廊展出的尺寸,就像是一些被锁定在画框中的特写镜头。用相机抓拍的快照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在硕大的面具中凝固不动。克洛斯以此来向我们表明,脸的生命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我关注的是一个人在刹那间的模样”,画家称,他的模特无须再次呈现拍摄瞬间的面貌,相似性只是其作品的一种“副产品”。相似性是一种对持久不变的面部表情的古老信仰,为了反驳这种由来已久的信仰,克洛斯惯于用宝丽来拍摄系列人像,再从中遴选一张作为油画素材。
1968年,克洛斯在第一幅自画像中描绘了他所有后续肖像的原型。在此之前,人们还从未见过如此纤毫毕现的写实主义作品。这种形式的放大并没有造成照片上常见的颗粒感。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从照片原型中破茧而出。在此,克洛斯的作品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一次——表现出一种轶事特征。据他的私人摄影师比凡·戴维斯(Bevan Devies)回忆,早在1970年,克洛斯就已将活跃的表情从作品中剔除出去:模特均以面无表情的正面像呈现,为的是在千篇一律的模式中见出其差别。1971年,为避免与照片的相似性,克洛斯有意使用了颜色,于是很快出现了水粉画、粉笔画和版画等一系列实验,克洛斯将彩色小方格作为一种风格手段来消解静止不动的图像平面,并通过各种绘画手段赋予脸以独特的生命。对脸的处理始终也是对图像和对面具的处理。另一个实验结果是1979年创作的复合式自画像,这幅肖像由九张宝丽来彩照组成,画面上的九个方格彼此错位,只有通过观者的视线才能将这些局部图像拼合成一张完整的脸。
克洛斯的早期作品大多以其友人和艺术家同行作为描摹对象,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开始以一种私人化的笔触为纽约艺术名流绘制肖像。过去那些在对照片的机械转化中看不见的方格,作为一个由无数网格组成的技术性表面得以呈现。人物的脸部特征在这些网格的“背后”显现出来。在这里,脸和数据载体间的不一致是一种有意而为的策略。在绘制过程中,脸从真实存在的绘画平面上剥离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脸的外观则被刻入了绘画表面的在场。
1989年,经历了一场危机的克洛斯在轮椅上重新投身创作,在新诞生的作品中,方格被赋予了另外一种特征,它们变成了再现的基本元素。这些“标记”(克洛斯语)近看像是一幅幅小画(图4),只有在特定距离之外,它们才会在观者眼中转变为一个生动的脸部平面。这些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排列的模块,构筑起整个画面。在评价这些作品时,克洛斯使用了含义不同于真实作品的“图像”(image)概念:“我的绘画和语言有关,绘画语法呈现了一个图像,而不是对表面进行修饰。”

这种艰苦的创作过程显得不合时宜而又独树一帜,它是向大众媒体中的图像消费发出的宣战,尽管作品采用了巨幅尺寸,创作过程却仍旧保存了脸的痕迹。早在1973年——那时的格栅还有些不同——克洛斯就曾对绘制像素的观点予以否认。在一次去往自己作品展的路上,摆放在报刊亭的一期《科学美国人》吸引了他的目光,在这本杂志封面上,人们熟知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肖像被处理为一个像素化的表面(图5)。克洛斯在随后的展览开幕辞中强调说,不要将他的绘画与数字技术作比。他表示自己绝不使用机器进行创作,因为他无法忍受“画面和我之间”有任何技术“界面”存在。因此,查克·克洛斯描绘的脸也可被理解为一种媒介批判,尽管它们首先对图像概念做了解构,将脸的可再现性置于危机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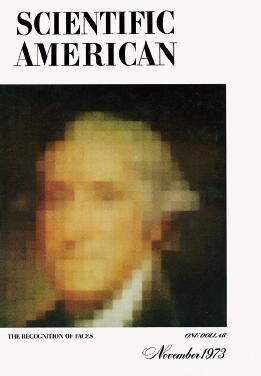
1944年12月,在为克洛斯做过一次模特之后,约翰·格尔(John Guare)对画家为其模特们安排的仪式做了精湛描绘。1988年,格尔曾为病中的克洛斯写过一部传记,似乎是为了回馈这一文学肖像,克洛斯又为格尔专门绘制了一幅肖像。为了拍摄作为参照的大尺幅宝丽来快照,格尔为克洛斯做模特长达五个小时,克洛斯则尽可能确保所有画面中人物的眼部及嘴部处在同一平面,在拍摄最后一张照片时甚至还确定了眉毛的位置。格尔记述了为克洛斯做模特的经历,称这些照片勾勒出一张“人的草图”,将一张脸转化为可以描绘的“风景”。在五个小时的拍摄过程中,光线始终起到了关键作用。克洛斯像一个电影导演那样一丝不苟地对光线进行控制,仿佛是在拍摄一幅幅剧照。格尔感到自己像是在倾尽一生来完成一场表演,过往生活一幕幕地在眼前重现。随后,画家将二十幅宝丽来快照挂在墙上,在与格尔讨论之后,克洛斯做出了最终选择,亲自确定了人物表情。
这一刻板的工作流程——为克洛斯做过模特的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与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曾对此有记述——见证了由脸的危机引发的图像危机。传统肖像中的那种对脸部相似性的描摹似已过时。在克洛斯这里,相似性一方面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则通过一种技术手法制造出来,其操作步骤可以被精确还原,仿佛是在执行编写好的程序。克洛斯借助一些固定不变的元素——“记号”,对脸进行还原。马里昂·卡乔里(Marion Cajori)曾花了三个月时间来拍摄克洛斯创作自画像的全过程,这位导演谈道,用艺术家本人的话来说,他想创造出“一个由呆板的记号组成的美而有力的图像”。但这个图像还不是脸本身,它拥有自己的生命,它必须对抗由机械式绘画行为构成的僵死语境,对抗比例失调的巨大尺幅。脸的危机在于,人们无法一对一地对脸进行复制,因为技术媒介时代的绘画拒不接受这样一种能力。曾经投射在一张脸上的画家目光,被一种客观中立的技术程序所取代,后者为最终呈现的脸部图像提供了担保。但即便当我们注视一张脸,以观者身份“置身于图像中”时,脸仍旧作为一种不可操控的因素,在远离一切复制技术的地方重新显现。
节选自《脸的历史》,德国著名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力作,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人出现在图像中时,人脸总是成为图像的中心。而与此同时,脸却仍以其特有的鲜活和生动,与一切将其固化为图像的尝试相对抗。在这部前所未有的《脸的历史》中,作者汉斯·贝尔廷探讨了脸和图像之间的这种张力。
本书从石器时代最初的面具开始,以现代大众传媒制造的脸为终点。汉斯·贝尔廷在宗教面具、舞台面具与演员的脸部表情、欧洲肖像绘画、摄影、电影、当代艺术中,发现了种种企图征服脸的尝试。而由于脸和人的自我都是一种鲜活的存在,这些尝试无一不以失败告终。生命不断地进入图像,最终却与一切再现规范和阐释标准相对抗。甚至近代欧洲的肖像绘画所生产出的也大多只是一些面具。电影虽然以无可比拟的私密性对人脸进行了展现,但这种将人类第一次真正付诸画面的诉求也宣告失败。
本书可谓是第一部从文化史、图像学角度探索“脸”这一主题的著作,极大丰富读者对“脸”这一最值得解谜之物的深入认识。充满了打破流行观点的真知灼见,是对漫长历史中诞生的人类自画像的一次引人入胜的探索。
注: 本站发表文章未标明来源“成功书画家网”文章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邮箱:1047780947@qq.com